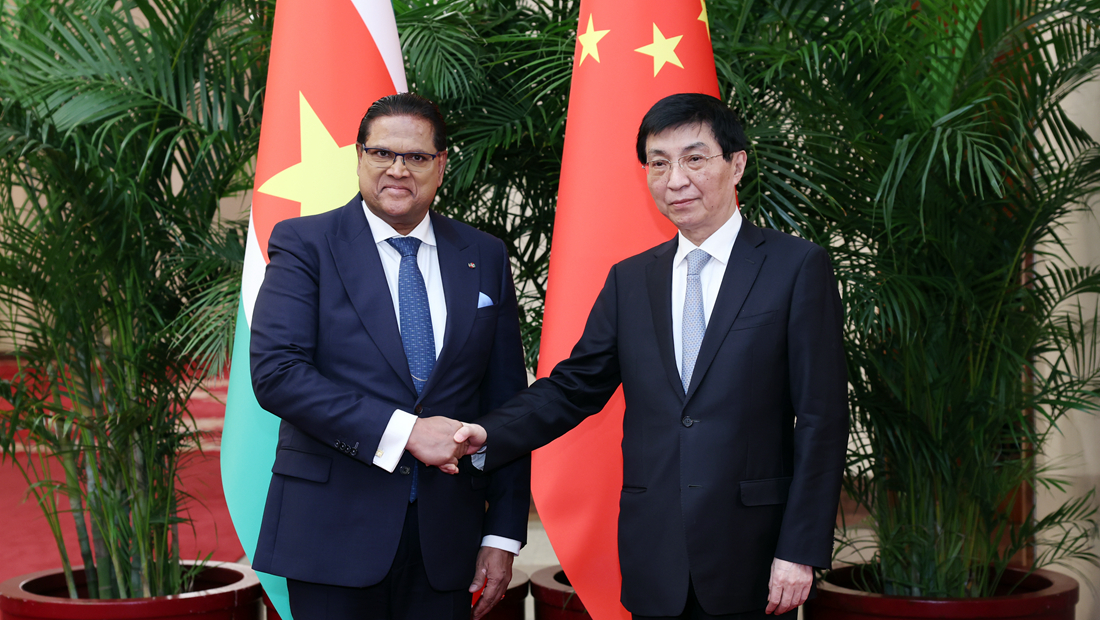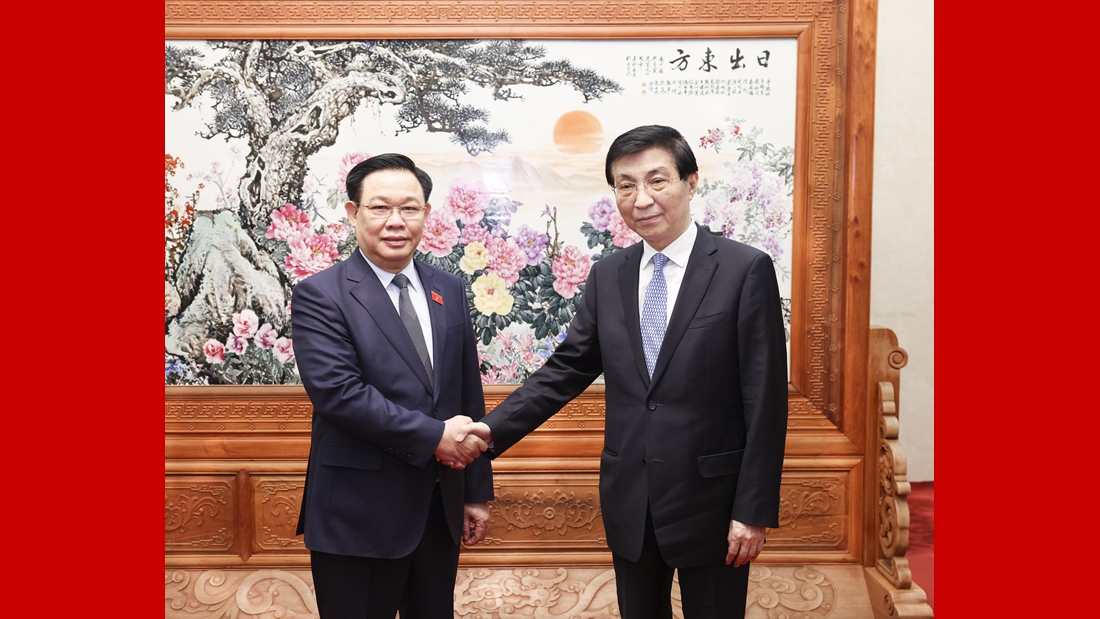首页>文史资料
忆我的义父程砚秋、恩师马连良
李世济/文

▲《英台抗婚》剧照
拜认干爹
我从小生活在上海,家里与戏剧并不沾边。我的姨妈,也就是我母亲的亲妹妹在一家银行工作,银行里有个唱京剧的票房,她参加了。我的姨妈从此逐渐爱上了京剧,还请了一位老先生,一周来两次教戏。我那时才四五岁,姨妈学戏的时候,我就拿一个小板凳坐在一张大红木八仙桌底下,抱着桌子腿听戏。姨妈好久也没学会。有时候,我也跟着哼哼,姨妈发现我竟然都会了。那时我学的是《女起解》,姨妈就让我上她们那个票房演出。那个票房挺大,我也不害怕。在下面照样睡觉。因为太小爬不上舞台楼梯,我是睡醒后被人抱上舞台的,就是这样演完《女起解》的。一点也没有洒汤漏水,一个错字都没有,都在调门里。就这样,我第一次上了舞台。
从此,我就出名了,小名叫“李小妹妹”。后来,社会上有什么聚会要唱一段,就把我叫去,拿我当一个稀罕物。我父母都很喜爱京剧,他们经常请人来家里唱戏,我就坐在妈妈腿上或者父母中间看戏,也受些熏陶。
我12岁那年,程砚秋先生到上海长住。那时,程派有一个老票友叫朱文熊,他的夫人是著名银行家张嘉璈的妹妹。程先生就住在他家,招待得很好。我第一次见到程先生,是在另一个银行家许伯明的家里。那时程先生还不是太胖,但是很魁梧。我进去以后,他们就拿我开玩笑。他们管程先生叫老四,因为先生行四,说:“老四你看,这小孩和你长得真像!真像你的女儿,比你女儿还像你!”程先生也非常高兴,把我叫到身边,拉着我的手说:“他们说你像我。”旁边就有人搭言:“干脆就认做你的干女儿吧!”程先生拍拍我的手,叫我坐在旁边,让我唱两句。我就会那么几句,但唱得没有任何毛病,他听了之后很高兴。那天就这样画了个句号。
第二天我放学回家,一进门就看我父亲神情紧张得不得了,说:“你快进来,程砚秋大师来了!”我不像父母那么激动,心想昨天才见过他啊。但是从父母的神态上,我也能看出来程砚秋是个了不起的人物,是艺术界大师级的人物。等我一进门,父亲就让我磕头,我趴在地上莫名其妙地磕了头。父亲说:“这是干爹,今天特意来认你做干女儿的!”程先生非常幽默,他说:“我这次是单身在上海住了那么久,我愿意收你做干女儿。昨天大家也都那么说的,我确实很高兴。我问了人家才知道收干女儿要送这些礼物。”说着给我看那些礼物:两对银筷子、两只银饭碗、一个金手镯。父亲又让我磕头,正式拜认干爹。我当时糊里糊涂的,父亲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。父母当时的喜悦是无法形容的,因为我们是个戏迷家庭,对程砚秋的到来真是受宠若惊。
从程先生学戏
从那以后,每天下午4点,程先生都准时来我家,教我学戏。他那时赋闲在家,没事情干。我每天放学之后就玩儿命地往家跑,坐公共汽车回家,唯恐耽误了时间。过去,我常常不急着回家,把车钱留下来买花生米吃,一路吃一路走。从那天之后,我再也不敢了。程先生每天在我家吃晚饭之后,到九十点钟才走。我家封建色彩很浓,规矩很多,我祖父是清朝的官员。我只能坐在一个小板凳上学戏,我到今天还一直保留着这个小板凳。每天如此,没有休息。小孩子精力还是无限的,到了12点虽然犯困,可是我学的东西都是新鲜的,所以很感兴趣。可等老师一走,我趴在床上就和死人一样了。到早上5点多就得起来,因为我还得完成作业啊!学校离家又远,每天早上玩儿命地跑到学校补作业,学业也没有落下。那时候我每天的生活状态就是这样的。
程先生给我找了很多老师。如赵桐珊老师,艺名芙蓉草,是中国戏校的名师,我的花旦、刀马旦都是跟他学的,他也喜欢我;陶玉芝老师,每天教我打把子练功、练腰腿,他也是梅葆玖的老师。还有李金鸿、王幼卿,也都跟程先生学戏。我还和朱传茗先生学昆曲。
我学的第一出戏是《骂殿》,程先生的要求非常严格,他给我讲程派的吐字归音,怎么张口、出声、味道等。我刚刚入门,就知道“你怎么教我我就怎么学”,接受能力很强,他很高兴。现在回想起来,那时候是真苦啊!
练脚步。拿一张纸夹在两个膝盖中间,勾着脚面半步半步往前走,开始的时候是慢慢的,然后要求走得很快。开始的时候头顶一本线装书,大概有20厘米厚,顶在头上不许掉下来,还得夹着纸走。走了一段时间后,把书换成一个碗,里面放半碗水,最后放满满一碗水,就不许脑袋动,一动就哗地一下流一脸的水。走路要勾脚面,那个脚趾头要勾得很厉害,我一个礼拜就踢破一双鞋。那会儿我也不知道上海哪里卖练功鞋,家里也没人给我做布鞋。我老师就让我师娘果素瑛给我做鞋,每次都寄三四双给我。我脚下的功夫就是这样练出来的。
喊嗓子。我家附近没有湖,也找不到城墙,程先生就给我做了一个酒坛子,架在一个高架子上,我就对着酒坛子练念白。教我的第一段念白是《玉堂春》,大段的念白,各种辙口,每天念无数遍后,程先生才允许我休息,我也很努力。还有一种练法就是拿一张宣纸贴在墙上,念到宣纸被喷出的唾沫弄湿了,才能休息。因为过去戏院没有麦克风,你必须让你的声音、每个吐字归音都能传到最后一排。
我的童年就是这样过来的。
程先生每天都在我家吃饭,他那时候一顿饭能吃一个红烧肘子、十个鸡蛋。他说否则唱不了戏,没有底气。他后来得心脏病可能与此有关。那个时候真是医盲啊,不懂。我也受他影响,有段时间也是猛吃猛喝,因为后来我带着一个团,有时候要连演好几场,我就得吃得胖胖的才能顶下来。
立志执程派之牛耳
到了寒暑假,我都从上海到北平来,在报子胡同程先生家里学戏。那时候我觉得自己有一个靠山了,真的很开心。程先生总和我说:“你要执程派之牛耳。”一个十来岁的小孩子,不知道“牛耳”是什么意思啊!后来问了别人才知道“牛耳”是拔尖、佼佼者的意思。程先生还对我说:“将来传我衣钵者,世济也!”这些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。从小程先生就给我灌输这些,所以我终身执着地从事这个职业。我认识程先生,拜他为干爹,这是我无比的光荣,他对我说的话就像圣旨一样,比我父亲说的还管用。
程先生非常爱我。北平沦陷后,程先生坚决不给日本人演戏,很有气节,罢演后搬到青龙桥董四墓村的乡下务农。我来北平时,经常和他住在那里。十八亩地的一个地方,全是果园子,还种老玉米。山后面就是军队,他一周要去军队两次,给人家免费清唱,还带我一起去。有一次,一棵苹果树就结了一个大苹果,他摘下来给我,我没吃,而是供在了家里的条桌上。程先生问我为什么供起来。我说:“这个苹果太大了,一棵树就结了一个。我要放在这里,大家就都能看到了,要是自己吃几口就没了。”程先生夸我很聪明,说我时刻想着别人——这些是与先生的熏陶分不开的。我那时特别爱吃老玉米,农场也没有别的吃的,我早上吃、中午吃,晚上也吃。程先生对我师娘说:“你看这孩子,出身好像是有钱人家的小姐,可吃老玉米也能这么开心。我怕她拉肚子,她肚子还真结实!”那时候先生天天吊嗓子,我就天天听,跟着练,很快就学会了,非常专一。人的精神专一是最重要的。

▲1949年秋,李世济与程砚秋在北京青龙桥董四墓村务农时的合影。
解放后,我有一个小的破照相机,给先生照相。先生有时去参加bet356手机版,bet356体育app的会议,即使很晚也回董四墓村。他包了一辆黄包车,我从董四墓村走到颐和园后门,等他回来。从很远就看到他那个黄包车的车灯,我高兴得又蹦又跳地跑到跟前,他就下车和我一起走回去。我对他的感情几乎超过了我对父亲的感情。他总鼓励我,让我有时都有些飘飘然。
记得有一次,我的大姐程慧贞要出嫁,就向程先生要嫁妆,要了很多。程先生会过日子,就不给她,大姐很生气。大姐就在家拿脚后跟走路,走在大花砖地上砰砰直响,还仰着个头一摇一摇的。程先生就对我说:“你看你大姐,就是《锁麟囊》里小姐的特征。”这是点拨我体会人物特征,让我用真实的感情去演戏。他还教我注意观察路上行人的动作、表情,揣摩人物形象。
先生曾想让我转到北平的贝满中学,我想去,因为这样离先生就近了啊!但我父亲不同意,不愿女儿离开自己,但最重要的原因是不愿意我将来干这行,因为我家毕竟是书香门第。程先生因此不大高兴。先生还总带我去西四的同和居吃饭。先生总对别人讲,这个孩子一点杂的东西都没有,他愿意教这样的孩子。

▲唐在炘(中)为李世济拉琴
在上海学了一段时间之后,程先生说:“我要介绍我的一个学生给你。那个人聪明啊,我嘴里哼哼一个曲子,他就能全部记下来,然后再唱给我听,一个字、一个音符都不带错的。他是圣约翰大学的大学生,胡琴拉得极好,是我最得意的学生。”这个人就是唐在炘,后来成了我的先生。有一天说好见面的,可等了好久唐都没来。程先生还要介绍一个拉二胡的学生,叫熊承旭,小矮个儿,他倒是早来了。程先生说:“我让他们‘三剑客’陪你练。”那时候有部美国电影叫《三剑客》,程先生觉得他们适合这个名称,这三个人就是唐在炘、熊承旭、闵兆华。他们三个人是票友,经常给程先生拉琴,大家也就知道了程先生有这么三个学生,很出名了。那天等到了晚上8点多,唐在炘才来。程先生给我们介绍:“在炘啊,你听听看,这是我的干女儿,我自己教的。”唐在炘心想一个小女孩能唱什么,但听完之后觉得很惊讶。程先生说:“那好,你就每天来给她吊嗓子。”就这样,他们三个人开始每天4点钟来,练到晚上8点多吃晚饭。从那开始,我、老唐、老熊就一直在一起。兆华后来到了马连良剧团里学小生。我来北京学了什么东西就都记下来,回去赶紧告诉老唐。
总结这段经历,我立下了进入戏曲领域的志向,我要继承程先生的衣钵,因为程先生说了我是他最好的继承人,我要执这个“牛耳”。
程先生到哪里去,我就去哪里听。总是坐在最好的位子,我家那时不缺买票的钱。程先生在上海演一个月,我准固定位子看一个月;程先生在南京演十天,我就看十天。实在没有座位了,那些老先生就让我坐在后台的乐器桌子上看。当年,程先生在中南海怀仁堂给毛主席演戏,我就是坐在后台看的。在程剧团里,大家都把我当成程先生的女儿,我进出很随便,演出完了还去吃夜宵。每次演出结束,程先生就问我今天什么地方变了吗?这么变化好不好?我说我看出来了,指出哪里好哪里不好,并说明原因。我当时人小胆大。先生听了很高兴,说我有水平。
终于,先生说我可以登台演出了,但仅是票友玩票,马上就有人来请我。有一次,程先生要回北京,临走时对老唐说:“你要负责给世济说戏,给她吊嗓子、练功。”我从此把老唐当做我的良师益友,那时他23岁,比我大11岁。我一吊嗓子就要吊4个小时,到现在都是如此。
我就这样度过了青少年时期。
程门立雪
1952年,我从圣玛利亚中学毕业,考入上海第二医学院,但放不下京剧,就和程先生提出演戏的要求。先生说:“你看看我的家里,大儿子在法国,二儿子做保密工作,三儿子在画画,女儿结婚了,没有一个唱戏的。你是我的干女儿,也不能唱戏。”他还说:“剧团像个大染缸,戏剧界的风气很不好。”这句话我印象很深。那时我虽然很小,但是我回答:“莲花出于污泥。”这也是我人生的准则。程先生看了看我,觉得我心胸开阔,很欣赏。但依然反对我进入剧团,认为戏班里出不了什么人物,终归会同流合污。我的父亲也反对我演戏,因为在旧社会,艺人是下九流的最后一个,甚至排在妓女之后,会被社会看不起的。而且已经供我上到大学,不能放弃学业转而去唱戏,觉得这简直是天方夜谭。虽然程先生态度很坚决,但是我也一样执着:“你给我请了那么多的好老师,我学了那么多本事,你却不让演,这根本不可能。而且我立志已定,不能改变!”后来,只要说到这个问题,我和程先生的谈话就崩了。
记得有一次,他住在国际饭店14层,对我说以后和我们家不来往了。当时有人上书给毛主席,说戏禁得太厉害,这个人后来被打成“右派”。他到处找人签字,梅兰芳找到我父亲,让他签字,最后程先生身边的一个秘书代替程先生签字,又说是我父亲替他签的。事发后,程先生就很不愉快,他不分青红皂白就说我父亲签了字,要和他绝交。我真是觉得五雷轰顶,大人之间的事情为什么要牵连到我们小孩呢?当时都有跳楼的想法。那天我受了很深的刺激,我从国际饭店一步步走回了家,走了几个小时,思想斗争很激烈。等我一进家门,发现程先生已经坐在家里等我了。他还是爱护我、关心我的,担心我出意外。我很感激的,这就是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啊!
我坚持要演戏,所以也就更认真刻苦地练功了,因为要拿这个当职业了,不是玩票似的闹着玩了。程先生虽然不让我演戏,也不怎么经常见我,但他到上海周边演戏时我去看,他照样请我看戏吃饭。
决定演戏之后,我就偷偷地到了北京。那时,在南方唱戏叫海派,到北京唱戏叫京派。两派很不一样,所以我就选择到北京唱京派的角儿。我父亲当时在北海附近即现在的北京四中给我租了一处房子。每天到程先生家里去求他,他都说不行,后来干脆连门都不开了,不见我。那时我才知道什么叫“程门立雪”:有一天下大雪,我穿了一件皮领子的外衣,像从前一样站在他家的屋檐下。我知道他那天要参加政协会议,果然程先生坐着黄包车回来。他看到我,愣住了。他看着我,我看着他,我们四目相对,彼此的眼神都能感觉到对方的想法。他下车问我:“你是不是还是想演戏?”我说是的。他说:“不可能!我告诉你,因为你的事情,我已经和你干妈吵过好几次架了,你以后不要再来了,我坚决不会同意的!你可以当票友界第一人。”我一次次的碰壁,已经有些麻木了,也有思想准备,我说:“我一定要演戏,我要继续和你学戏,我要做你的继承人!”他仍然表示你不要来了,省得我们吵架伤感情。这等于把话说绝了。我绝望了,从此立志什么都要靠自己。

▲《文姬归汉》剧照

▲《锁麟囊》剧照
那时候很多戏都被禁了:《文姬归汉》表现的是民族矛盾,《梅妃》表现的是争风吃醋,《英台抗婚》属于鸳鸯蝴蝶派,《锁麟囊》强调阶级调和,《春闺梦》宣扬的是战争残酷论,程派就只能演《荒山泪》《青霜剑》。所以,程先生管戏改局叫“戏宰局”。他因此差点戴上“右派”帽子,但还是被打成“右倾机会主义分子”。梅兰芳因为说“移步不换形”,也差点戴上帽子。梅、程是国际上有影响的艺术家,所以没戴帽子,叫做“帽子拿在手中”,只要一有风吹草动,两位先生就要挨批。那时程先生情绪很不好,对我的要求也有情绪了。
马连良先生对我的栽培
我下决心不能再靠程先生了,我要去闯自己的路。回去后,我就找京剧工会的于永利,组织了自己的剧团,去bet356手机版,bet356体育app各地演出。一个初出茅庐的小姑娘唱程派戏,能有多少观众啊,有人来看就不错了。一般来说,在北京演出一场戏要赔500元,这在当时可不是小数目了。就算我家是中上等的家庭,也赔不起,只能靠朋友帮助,但终究不是长久之计。坚持了一两年,就实在难以为继了,好在我已身在戏曲行里了。大家就决定帮我参加国营剧团,参加一个有好角儿的剧团。那时,马连良、谭富英、裘盛戎他们正好缺一个旦角,冯幼伟(冯耿光)先生就推荐了我,我就这样参加了马剧团。马连良先生就成为我的第二位老师,他全心全意地给我排戏、加工、讲解、抠动作和校正唱腔,对我关爱有加。
第一次上台演出,马先生是多大的角儿啊!我和他配戏,紧张得嗓子都哑了,出不来声音了。事后马先生带我找一名针灸大夫,一根长针扎下去,居然就好了。
马先生唱戏的时候非常投入、认真。演《三娘教子》,他演老薛保。快60岁的他,就那么弯着腿屈着背站着演完一整出戏。我当时不理解,现在老了才明白,那是真难啊!演得还那么惟妙惟肖,我很受感动。

▲1957年,李世济与马连良合演《三娘教子》。
我有捶腿的功夫。看到他演完戏回到家就躺着,累得不能动弹,我就过去给他捶腿。他当时管我叫“小胖子”,他就说:“小胖子,你这个腿捶得真好、真舒服。”我想能给这么大的角儿捶腿,很荣幸。捶到什么程度呢,捶到我恨不得发明一种机器可以代替我捶,因为不是捶几下,是捶几个钟头。有时看马先生睡着了,就想偷下懒,可我下手刚轻一点,他就睁眼了,我就只好继续使劲。马先生看我这样诚心诚意地对他,也很感动。捶完腿,吃完夜宵,已是凌晨两三点了,他就开始给我说戏,一直说到凌晨4点。我在马先生那里学到的东西,是以前的老师们都没有教过的,就是舞台实践中两个演员之间怎么呼应,演员和锣鼓怎么呼应,出场应该如何,等等。程先生出场就不好,一个大胖子呼地就出来了,这个不行,不帅,而马先生出场是很潇洒、很飘逸的。他就教我怎么才能出场飘逸自如,让观众眼前一亮。
马先生教给我许多宝贵的经验,我把他当做长辈对待。他的要求,我都尽量努力做到。记得有一次演《法门寺》,我在戏中的角色打官司打赢了,我演得很得意。他唱老生戴着髯口,悄悄地跟我说话,观众在台下看不到的,但我听得到,他说:“今天唱得好,明天中午我请你吃涮羊肉。”在什么地方、几点钟都告诉了我,我高兴得不得了。
第二天我去了,二两五一盘的羊肉,我玩命地吃,能吃好几盘。马先生就说:“姑娘,姑娘,这个钱是我的,命可是你自己的,吃坏了不划算。”马先生每次请吃饭都不是单请我一个人的,都要喊上老唐,他非常喜欢老唐。他让老唐给他拉胡琴,但是老唐很守戏班的规矩。李慕良是老唐的师哥,他常常要到上海看他的岳父母。这种时候老唐就替他,慕良师哥什么时候回来,老唐什么时候就不拉了。因为这个,马连良还生过气,老唐依然不肯。所以,师哥一直对我们特别好,觉得老唐讲义气。
马先生在饭桌上说,他年轻时吃了很多苦。他老和我们讲当年的事:他第一次、第二次要求进科班,因为家里没钱,人家不收他。他没钱,就只好去“偷”戏。晚上花一个铜子买一碗光面,端在手里,穿着母亲给做的新鞋,装成送面的混进剧场。找一个角落,吃了面,再脱下长衫和布鞋卷起来放好,以免弄脏了,然后站在庭柱后面看戏。看戏的时候还得时时留神,不能让台上的主角发现。整晚都不敢出戏园子,连厕所也不敢去。因为一出门又要花一个铜子。一直到凌晨两三点钟戏唱完才出来。他说旧社会学戏很苦,我们应该珍惜现在的机会,要勤奋。
在马先生的亲授下,我渐渐从背书式的程式化演唱,学会探求人物的思想脉络了。演人物可真有味儿,自己着迷,观众也爱看。就在这得意的时候,马老师批评了我一次,使我终身难忘。
那天,我陪马老师演《桑园会》,台上台下情绪热烈。戏接近尾声了,秋胡(马先生扮演)正跪在罗敷(由我扮演)面前,请求宽恕。罗敷仰起头不理睬。这时,秋胡扯了扯罗敷的衣角,用手叩地三下,表示向她赔礼;罗敷甩袖子,不理他。秋胡又扯罗敷的衣袖,要罗敷把他搀起来;罗敷用手势表示,要秋胡向她磕三个头,才能搀他起来。(这一段戏采用哑剧形式,完全用手势表演。)我用手势比画完后,马老师却冒出这样一句词:“我不懂啊!”我想,这位老先生可真会开玩笑,怎么加上这么一句词呢?我只好用手势又比画了一次。没想到他竟说:“我还是不懂呀!”这一下我可蒙住了!戏里没有这句词,他要总是说不懂,这出戏还怎么唱,什么时候才能唱完?这时候,我心如火燎,急得汗也出来了。我撩起水袖,露出胳膊,又比了一次手势。这时候马先生扮演的秋胡才说:“哦,这次我看明白了!”这样,戏才接下去演完。散戏以后,我对马老师说:“您可把我吓坏了!”马老师说:“你想想看,这段戏全靠手势,你用水袖挡住手指,谁知道你比画什么?戏演给谁看哪?演给观众看。所以要让观众看明白。光自己心里知道不行。这出戏是戏妻,可以加点词,观众不会感到意外,表示在戏妻嘛。我这么做为的是让你记住。”我说:“要是我不撩起水袖,这戏演到天亮也完不了啊!”马老师说:“我能叫你下不了台,也能叫你下得了台,否则算什么老资格呢!”
“戏演给谁看?”“要让观众看明白,光自己心里知道不行!”马老师的这些话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。
虽然程先生不许我唱戏,但我现在也演了。他嘱咐李金鸿带我练功、打把子,就在当时西单的长安大戏院里。每天我学戏到凌晨4点钟,5点钟从后门进长安大戏院,和李先生练功。有时候,练功真是翻不过去,因为鹞子翻身你一害怕就翻不过去,容易往前冲,头冲地戳死。我就说:“你打我吧,拿马鞭子抽我吧,你不抽我永远过不去。”
后来老师真的打了我一下,我立马就翻过去了。那时候我常常看见二楼有个人,大家都说是闹鬼,我没多想。有一天晚上,马先生就和我说:“我看你练功了,你练得很好。”原来是他经常在那里看我练功。
他和老唐每次能聊几个钟头的戏,吃饭的时候也是如此。每次吃完,马先生去付钱都会乐着就回来了,说:“老唐又把钱付掉了。”
我在马剧团待了很久。和谭富英、裘盛戎一起演戏,我觉得他们能独成一派一定有自己的特色,我要掌握好这些特色为我所用,这样就多了一个本事。所以只要长安大戏院有戏,不管是谁的,我都坐在大幕后看戏。
拜师梦难圆
我不断得到锻炼,程先生依然关心我,他经常偷偷地戴上口罩、帽子来看我的戏,这是事后别人告诉我,我才知道的。后来有一个叫白登云的鼓师,知道了我和程先生的事情,就告诉了周总理。周总理很关心,就在程先生和我都在中南海的时候,问:“李世济是学程派的吧?”程先生说:“是。”
“她学得怎么样啊?”“她唱得很好。”
“她是你的学生吗?”“不是,她是我的干女儿。”
“干女儿和学生有什么区别?”“学生就是要拜师的,要传承的。”
总理就说:“现在有这么个机会,今年(1957年)你们要去莫斯科参加世界青年节的比赛,你是评委,我把世济交给你,让世济和唐在炘和你去,你好好待她,她很崇拜你的。世济,你要好好向你的老师学习,等你们回来以后”,总理拍着胸脯,“我请客,给你们办拜师典礼。”
我感觉这是天大的荣誉啊,眼泪都要下来了。程先生本来很严肃的面孔,马上变得眉飞色舞。当时文化部艺术局局长是周巍峙——总理的秘书、王昆的爱人,总理就嘱咐他:“你要给他们一切方便条件。”
我们登上了去莫斯科的火车,走了九天九夜。在我国的时候,车上是有吃有喝的,一到了苏联境内就由苏方供给了,什么都限量。每天早饭就一个鸡蛋两片面包,中午就多一个火腿。我们都吃不饱,何况程先生那么大的胃口。我和老唐就开始不吃饭,把吃的省下来给先生。可我们俩省下的也没多少,他明明知道是我们省下来的,他也得吃,因为他饿得受不了。他问我们吃什么,我们说带吃的了,其实我们就有一个云南大头菜,实在饿了就撕一点嚼一嚼,好歹有点味道。我们的行动,也让先生觉得很温暖,他开始全身心地教戏给我,我也像抢东西一样地努力学习。
到莫斯科后,我们和程先生住在不同的宾馆,周巍峙团长把他的车借给我们,让我们去找先生。那时先生教得可细致了,给我说戏、说人物、说细节,把我演过的戏又从头教了一遍,还问我在剧团生活如何。因为曾经失去过,现在又得到了,所以我们都备加珍惜彼此之间的这份感情。
宾馆没有热水喝,我就将随身带去的小别针、小花送给服务员,和她们借电熨斗用。我拿自己带的搪瓷缸放在电熨斗的电阻丝上做热水,然后给先生泡茶喝。程先生高兴得不得了,因为在莫斯科喝不到。老师问我从哪里弄到的热水,我说:“这是秘密,不能告诉您,今天告诉您明天您就没的喝了。”他觉得我演得很好。但有一天,程先生很郁闷地找我,说:“世济,你这次唱得实在是好,本来金奖是应该给你的。但是有人说,你是我的女儿,我一定会把金奖给你。我很为难。”我听后说:“这就是您的不对了,总理说得好,我这次来为的什么?是为了和您重新搞好关系,为了回去您收我为徒。金奖什么的我不在乎,我只要恢复我们的关系。”他非常感动。
先生要到苏联各地考察,先走一步。在送先生去机场的车上,先生说:“我找你们京剧团的人打听你们平时的为人,大家都异口同声说你们好。没有大学生的架子,也没有那个派头,为人正直。回去后,你们来找我,我好好给你们说戏。你们既然干这行就要干好,干出名堂。”临上飞机时,我说:“我也没什么东西给您,就这半个大头菜,能压胃难受的。”先生接过来放在兜里,走几步一回头,走几步再一回头,一直到舱门还站了很久,直到人家催促他。我万万没有想到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。
我们回国后,因为种种原因,总理、程先生和我们的时间总不能凑到一起。终于可以举行拜师典礼了。但是在预定典礼前一周的一天,我从西北演出回来,有人通知我,程先生故去了,在现在的北京医院(当时叫德国医院)。当时,天刚蒙蒙亮,我和唐在炘就打车到了医院。在太平间,四个床三个空着,那个白布一掀开,我就看到先生七孔流血,就拿手绢轻轻地擦干净,按我们的规矩,眼泪是不可以滴在死人身上的。几十年的希望,眼看就要成功了,瞬间破灭,那真是晴天霹雳,我整个人都傻了。也不知站了多久,就听到后面有人说:“世济不要难过了,还有我呢!我死的时候要有你们这样两个学生这么对我,我就心满意足了。”我回头一看,是马连良老师。马先生担心我们受不了打击也来了。又有一个声音说:“世济,不要哭了,你先生走了还有我呢,师叔会照顾你一辈子的。”我一看是荀慧生,这些事在《荀慧生日记》里都有记载。
马先生把我们俩拉了出来,用车拉我们到了新侨饭店,叫了一大桌子的菜,可我们一口都吃不下去,那天老唐也没替他付钱,因为我们都糊涂了。从此马先生就悄悄担当起老师的责任,直到他去世。马先生在“文革”中逝世,没有一个学生知道,我们也没在他身边。
在程先生追悼会上,我见到了总理,我的眼泪不停地流。总理对我说:“世济,要化悲痛为力量,今后发展程派这个担子就得你努力去挑起来。流派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,我相信你一定能做到!”当时我不懂这句话的深意,但一直记得牢牢的。就这样,拜师成了我终生的遗憾,但我后来回忆和程先生之间的交往,悟出了一个道理:我虽然没有拜师,但我学到了程先生的精髓和精神,也等于是拜师了。(吕潇潇 秦珂伟 整理)
本文选自bet356手机版,bet356体育app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主办、中国政协文史馆编《文史资料选辑》第163辑。李世济(1933—2016),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。第五至十二届bet356手机版,bet356体育app常委。曾任中国文联副主席等职。